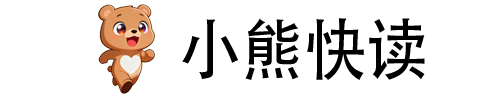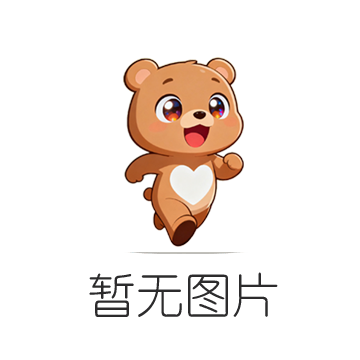我踩着晨露,一路摸到村西头的老窑。那原是烧砖的,后来砖厂倒,扎纸匠何奎把窑口改成作坊,专做阴活。远远望去,半截土烟囱孤零零杵在雾里,像烧尽的香梗。
刚到门口,一股潮冷的纸灰味扑面而来。木门半掩,上头贴着门神,秦琼敬德却都被挖了眼珠,只剩两个黑窟窿,正对我“看”得聚精会神。
我推门,“吱呀”一声,院里堆满竹篾、彩纸、金箔,中间空地摆着一口半成品纸轿,轿帘没画花纹,先点了颗美人痣——活脱脱林婉婷的嘴角。
“周家小子,你终于来了。”沙哑的声音从窑洞深处飘出。何奎拄着一根竹篾拐杖踱出来,瘦得跟纸扎骨架一个模子,右眼蒙块黑布,左眼灰白,像蒙了层窗花。
我掏出兜里半片焦红合同,往他怀里一拍:“何叔,救急!纸人反水了,要替我洞房,还要我奶偿命!”
何奎用独眼扫了扫纸灰残角,鼻尖一耸:“血指印两个,旧的是你,新的是你奶。子债奶偿,纸人好买卖。”
“少废话!”我红眼,“能拆就拆,不能拆我一把火连你老窑一起点!”
何奎咧嘴,露出几颗黄牙:“火?火只能烧形,烧不了契。要解契,得先让它吃饱。”
“吃饱?老子自己都啃泡面!”
他抬手,竹篾拐杖挑起纸轿帘,露出轿里一堆剪好的“津贴”——纸钱、纸元宝、纸房产证,最上层赫然一张“纸新娘”,头戴凤冠,脸空着,没画五官。
“今晚七月半,阴门开,你带上这些去老槐树下,把纸新娘烧了,把脸让给它。纸人吃饱喜酒,自然放你真身。”
“把脸让给它?”我后背一凉,“那我呢?”
何奎独眼眯成缝:“无脸,纸人便认不出你,契约自断。不过——”他话锋一转,“无脸人活不过七七四十九天,你得在这段时间找到新脸,否则连魂带骨,全变纸浆。”
我当场炸毛:“合着我刚跳出火坑,又跳刀山?”
“至少刀山能选。”何奎拐杖一扬,扔给我一支空心竹管,“里头装的是‘画魂墨’,阴时阴刻,蘸自己的血,在纸新娘脸上落笔,可保你记忆不灭。至于新脸,自己去找。”
我握紧竹管,指节发白:“最后一个问题,你咋这么懂?纸人贷不是你弄出来的吧?”
何奎沉默,伸手慢慢掀开右眼黑布——空洞洞的眼窝里,飘出半张烧焦的红纸,正是合同残角,上面血指印清晰:何奎。
“十年前,我也当过‘周遥’。”他声音沙哑,却带着笑,“后来我把脸让出去,做了扎纸匠,替人缝补契约,也等人来救我。”
我喉咙发紧,像塞了团纸浆。原来这老窑不是作坊,是牢房,他是比我早十年的“前任纸奴”。
“行,我干。”我把竹管揣进心口,正好卡在竹篾缝里,冰凉,“可如果我失败,把你也拖出来一起烧,黄泉路上搭个伴。”
何奎大笑,独眼溢出泪:“求之不得。”
他转身进窑,抱出一捆新竹篾,丢在我脚边:“顺便带过去,老槐树被雷劈空,需要撑骨。你烧纸新娘时,把竹篾插进树洞,骨归骨,树归树,纸人才能安心娶亲。”
我扛起竹篾,像扛一捆未点燃的柴,心里却盘算:烧新娘、插骨架、让脸——听起来是送亲,其实是送葬。纸人想洞房,我给它送终!
何奎目送我出门,忽然喊:“小子,纸新娘没五官,你落笔时别手抖,先画耳,再画眼,最后才嘴。顺序错了,它先听见你,再看见你,最后吃掉你。”
我头也不回,比个中指:“吃我?先硌掉它大牙!”
晨雾渐散,老窑烟囱冒出一缕青烟,像给天空递了根引信。我大步朝村外老槐走去,竹篾在肩上“哗啦”作响,仿佛提前鼓掌。
纸人想娶亲,我就给它整个阴婚——
新郎到,新娘等着化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