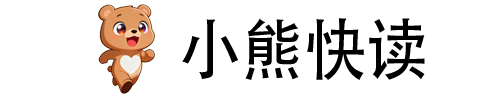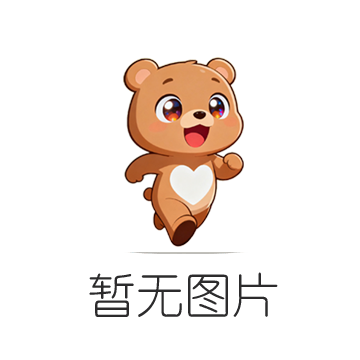蟹壳青的天边刚翻出一点鱼肚白,我把车扔在国道边的野沟里,步行进村。不是装低调,是怕发动机声惊了狗——更怕狗一叫,纸人先我一步知道我回来了。
胸口竹篾缝被风吹得“咔啦咔啦”,像几块碎骨在鼓掌。我摁着那地方,低头翻沟里的玉米杆,一股霉潮味直冲脑门,却让我莫名安心:活土活气,总比车厢里的纸灰强。
顺着田埂走十分钟,村口的百年老槐树先撞进视线。树干空心里早年被雷劈过,焦黑一半,却偏往另一边抽枝,像人歪脖子笑。小时候我爬上去掏鸟窝,奶奶就在下面喊:“小遥遥,别折腾,老槐是阴差歇脚的地儿!”
如今再看,那树真像打着瞌睡的门卫——枝条无风自动,“沙沙”冲我鼓掌。我加快脚步,刚靠近,一股纸灰味从树洞飘出,冷得跟冰箱漏气似的。我心里咯噔:纸人比我先到?
树洞里突然“扑棱”一声,飞出一张黄表纸,啪地贴我脸上。我撕下来一看,上面用朱砂写着我的生辰八字,字迹却像被水泡过,糊得血泪横流。纸背面还粘着半截红绳——正是我三个月前按血印的那根。
“操,连证物都准备好了。”我捏着纸,心里骂娘。看来纸人不是追着我,是算准我会回来,提前布好迎宾大道。
抬头再望,树洞深处隐隐透出红光,像有人点了盏小灯笼。我咬咬牙,掏出火机,把黄表纸凑火苗上:“先烧个开门红,给你减减晦气!”
纸刚触火,树洞里突然传出“哇——”一声婴儿哭,尖得指甲挠玻璃。我吓得火机掉地,黄表纸趁机挣脱,飞进洞,火灭,纸完好。紧接着,树洞边缘探出一只小手——白纸卷成,关节用订书钉,五指尖尖,冲我勾了勾。
“来呀,签字呀。”声音像奶娃娃,却是我成年后的嗓音,诡异得要命。我抡起手里的木棍,照手就砸,“噗”一下,纸手碎成雪片,可雪片没落地,全往我脸上扑,一片片往竹篾缝里钻。
我连忙吐口水,边拍边退,脚下一绊,“咕咚”坐地,屁股正好压住火机,“啪”一声炸响,塑料壳碎成渣,火苗却蹿起半尺高,把飞来的纸雪瞬间卷成黑蝶。
树洞里哭声戛然而止,只剩焦糊味。我喘着粗气,刚想爬起,背后“吱呀”一声——村道尽头,奶奶家院门自己开了。那扇老木门我熟得不能再熟:门额上“勤俭持家”四个字,是我爸生前用红砖磨的,如今却蒙着一块白布,像给门戴了孝。
我心里一沉,也顾不上拍土,撒腿就往院里跑。院里静悄悄,鸡不叫狗不跳,只有堂屋门槛上坐着个人影——背对我,肩膀窄窄,穿藏青布衫,脑袋包白头巾,正是奶奶。
“奶!”我喊一声,声音劈叉。那人影缓缓回头,我却猛地刹住脚——
不是奶奶,是个纸人。
脸用我的黑白照,腮红新鲜,嘴角裂到耳根;身子却套着奶奶的外套,空荡荡的,风一吹,袖口里飘出几张黄纸,落在我脚边,上面全是血写的“遥”。
纸人抬手,对我招了招,关节“咔啦咔啦”,像老槐树脱枝。我血冲脑门,弯腰捡起一块砖头,抡圆了砸过去,“噗”一下,纸头飞起,在半空打了个旋,落在供桌上,正好盯着我。
无头身子却不停,站起来就往堂屋走,步子轻飘,却目标明确——供桌正中央,摆着奶奶的遗像。黑白照片里,老人笑得慈祥,面前香炉插着三根香,香头红得诡异,像刚点。
我脑袋“嗡”一声:谁说我奶死了?!
可遗像、供桌、长明灯,一应俱全。灯罩里跳动的不是火,是一张小小的纸脸,一边燃烧一边冲我笑。
我扑过去,一把拔掉香,把长明灯掀翻,灯油洒了一桌,火舌“呼”地窜起半人高,纸头、纸身子瞬间卷进火里,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噼啪声。
火光里,供桌抽屉被热气顶开,露出一块红纸——正是我签的那份合同。火苗舔过去,纸边刚卷,我伸手就抢,烫得指尖起水泡,也硬把它拽出来。
红纸正面,我的血指印旁,多了个新指印——小一圈,指纹细密,是奶奶的。我眼泪一下就涌出来:老太太为了给我擦屁股,又按了一次血印,把债往自己身上揽!
火越烧越大,房梁上的纸灰被热气卷起,在堂屋盘旋,最后竟排成一行字:
“子债奶偿,天经地义。”
我咬着牙,把红纸对折再对折,塞进贴身口袋,贴着肉,烫得心脏发抽。
“奶,我回来了,谁也别想替你偿!”
我抄起门后的顶门杠,一头扎进火里,把燃烧的供桌挑翻,火星雨点般落下。纸灰、木屑、竹篾,在火中扭曲、蜷缩,发出细小尖叫,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
热浪烤得我脸皮发紧,胸口竹篾缝却灌进凉风,火借风势,“呼”一声,把堂屋中央的年画财神也卷进去。财神脸烧得扭曲,黑灰里露出真正的底色——一张空白的纸人脸,没画五官,只留着两个洞,像等我填名字。
我抡圆顶门杠,把年画戳下来,踩在脚下,狠狠碾:“想让我填?行,我填你骨灰盒!”
火舌舔上屋梁,木头“噼啪”炸响,再不撤就得陪葬。我最后扫一眼奶奶的遗像,玻璃已烤裂,可老人眼神依旧慈祥,像在催我快走。
我退到院中,把顶门杠往地上一插,掏出打火机,点燃口袋里的红纸一角,对着火海大吼:
“看清楚!合同我带走,命我自己还!谁敢动我奶,我让它连灰都剩不下!”
火苗舔上指尖,我却感觉不到疼,只听见“嘶啦”一声裂帛——红纸燃尽,火海里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。
同一秒,院外老槐树“哗啦”一声,所有叶片同时翻面,露出灰白的背,像给整个村子戴孝。树干空心里,那点红光“噗”地灭了,只剩青烟袅袅,被晨风卷着,飘向村外玉米地。
我跪地,给堂屋方向磕了三个响头,额头沾满泥灰。
“奶,等我,我把根儿彻底刨了,再回来给你养老。”
我起身,把烧到一半的红纸角塞进胸口竹篾缝,让它贴着骨头。灰烫肉,疼得我直哆嗦,却也让我无比清醒:纸人不是想要我命,是想要我“认账”。
行,账我认,但怎么还,得按老子的方式来!
天边已翻出鱼肚白,我回头望,老槐树歪着脖子,枝条无风自动,“沙沙”作响,像在鼓掌,又像在告别。
我冲它竖起中指:“别急,下一个轮到你。”
我转身,朝村外扎纸匠的老窑奔去。晨风吹在后背,凉丝丝,却不再带纸灰味,而是一股焦糊,像给黑夜点了最后一把火。
火是我点的,灰也得是我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