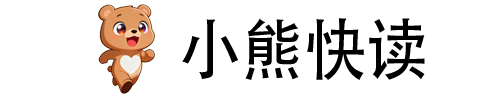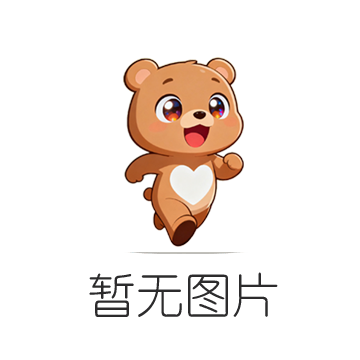我扛着竹篾往村北口走,太阳刚落山,天边最后一道霞光像被剪刀裁开,红得刺目。老槐树的影子拖得老长,枝丫张牙舞爪,像给黑夜搭好了戏台。
我把竹篾往地上一扔,看了眼手表——19:55,离阴门开只剩五分钟。何奎给的“纸新娘”躺在我脚边,薄薄一层,风一吹就鼓起来,好像偷偷在笑。脸还是空白的,没耳没眼没嘴,我却总觉得它在盯着我。
我咬破指尖,把血挤进竹管,和黑墨搅匀。竹篾缝里的风立刻兴奋了,“嘶嘶”往管口钻,像等着吸第一口烟。
“别急,今晚管饱。”我嘟囔,蹲下身,按何奎说的顺序,先画耳。毛笔刚落纸,“滋啦”一声,纸新娘的脑袋竟自己侧过去,空白的脸凑到我指边,像饿猫闻腥味。
我手一抖,血墨晕开,耳朵成了畸形。刹那间,老槐树所有的叶子同时翻面,“哗啦”一声,灰白背面在暮色里排成一片纸钱海。
“稳住,再画眼。”我深吸气,笔尖往下戳。两点朱红落下,纸新娘猛地弓背,胸腔位置“扑”地鼓高,又“咝”地瘪下,好像深吸了一口气。两点晕开,成了两个空洞的眼窝,黑得见不到底。
最后一笔嘴。我换支粗笔,蘸满血墨,刚要落笔,村口土路忽然响起“咚咚锵”——铜锣、唢呐、小鼓,齐刷刷飘过来,调子却是丧乐,拖得老长。
我抬头,一队“人”影从暮色里走出,个个两颊腮红、眉眼死板,花轿、灯笼、旌旗一应俱全,全是纸扎,被夜风撑得鼓鼓囊囊,像充气玩具。队伍最前头,一匹纸马,马背上坐着纸新郎——脸是我的黑白遗照,嘴角用朱砂补出夸张弧度,红灯笼一照,亮得渗血。
纸马每走一步,关节就发出“嚓咔”脆响,像有人拿剪刀修边。它身后,四个纸轿夫抬着红轿,轿帘半掀,里面黑洞洞,专等我画的这张脸。
我瞬间明白:这是迎亲队,来抬新娘,也抬我。只要我把嘴画完,纸新娘就能开口说“愿意”,然后轿帘落下,我这张活脸就得让位。
“想得美。”我咬牙,把粗笔往地上一扔,掏出火机,直接点纸新娘的空白嘴部。火苗“噗”地窜起,纸新娘发出婴儿啼哭,四肢拼命扑腾,像被按住的无脸猫。
火借风势,眨眼卷到腰。我趁机扛起何奎给的撑骨竹篾,对准老槐树洞,“咣咣”往里插,一连三根,把树心撑成三角架。竹篾末端刻满符,一沾树汁立刻变黑,像墨线浸油,迅速爬满树干。
迎亲队察觉异动,唢呐调子猛地拔高,变成尖锐哨声。纸新郎回头,黑白脸在灯笼光下裂出一道口,直抵耳根,像笑又像怒吼。它抬手冲我一指,纸轿夫立刻扔下轿子,四肢着地,关节反折,蜘蛛一样朝我爬来。
我火机往地上一撩,把剩下的血墨全泼出去,“轰”一声,地面窜起一圈火墙。纸轿夫撞进来,火舌顺着竹篾纹路爬遍它们全身,眨眼烧成骨架,风一吹,散成漫天黑蝶。
火墙后,纸新郎骑马踱步,火星溅到它身上,却只烧出几个小洞,露出里头更白的纸层——这家伙比手下耐烧。它慢悠悠拔下胸前一朵红花,花瓣是剪薄的宣纸,迎风一抖,“哗啦”展开成一张红纸,正是合同原件,上面两个血指印鲜艳得刺眼。
它把红花往外一抛,纸瓣在空中旋成圆环,像给火墙开了个门。纸马四蹄踏火,一步一焦黑,直直朝我逼近。我胸口竹篎缝立刻兴奋,“咔”地张大,像迎接老朋友。
我暗叫不好,转身往树洞跑,火机往竹篾骨架上一点,“轰”的一声,树心三角架燃起雄火,老槐树空壳瞬间变成大烟囱,火舌直冲天。
纸马在火前三米急停,纸新郎被惯性甩下,正扑向我。我抡起带火的竹篾,照头就抽,“啪”一下,纸脸被抽成两半,上半张飞进火堆,下半张还冲我咧笑,朱砂嘴角滴出血墨。
我补上一脚,把它踹进树洞火心。火焰“呼”地裹上去,纸身卷成卷,发出极细的笑声:“签字……”
火越烧越旺,把整个夜空烤成暗红。迎亲队的灯笼、旌旗、轿子,全被热流卷进火场,像一场倒放的送葬。纸新娘在地上翻滚,火已烧到肩膀,空白嘴部终于裂开,发出最后一声啼哭,随后化作黑蝶,腾空而起。
我仰头,看见漫天灰蝶盘旋,渐渐拼成一张巨大的脸——没有五官,只有轮廓,像等待我落笔的最后画布。我摸出口袋里仅剩的血墨,对着天空一举:“想要脸?自己来拿!”
灰蝶轰然散去,火场“噼啪”作响,再无声息。我跌坐在地,胸口竹篾缝被热浪烤得卷曲,却不再灌风,像被火漆封了口。
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叫,七月半的子时,过去了。
我喘粗气,看手表——00:00,阴门合。纸新郎、纸新娘、迎亲队,全成了树下那堆冒着青灰的渣。
火还在烧,我却笑得比火更旺:“洞房?洞你妈的火坑!”
起身,我朝火堆重重啐了一口血沫,转身往村里走。背后,老槐树“咔啦”一声,被火烤裂的树皮缓缓剥落,露出里头雪白的新层——像一张刚裁好的白纸,等待下一个签名。
我头也不回,把背影留给它。
要画脸,可以,但得先问问我这把火答不答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