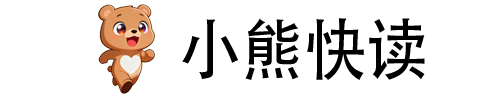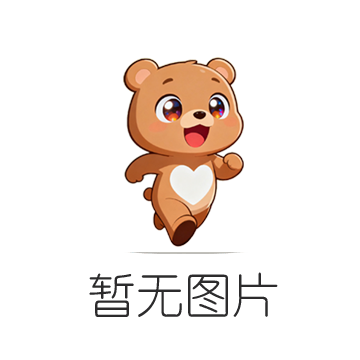液氮的嘶鸣声渐渐弱下去,像垂死者的最后喘息。我瘫在冷冻舱旁,胸腔里的菌核搏动变得迟缓沉重,每跳一下都牵扯着肋骨的钝痛。皮肤下的灰斑在低温中褪成淡灰色,但指尖触碰时,仍能感到细微的蠕动感,像冬眠的蛇在皮下苏醒。
通风管道传来金属撬动的巨响,刺眼的手电筒光柱划破黑暗。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惊呼在实验室里回荡:
“老天!这地方是个屠宰场!”
“检测到生命体征!角落里有一个活的!”
防化服摩擦的窸窣声逼近,几个模糊的人影在液氮余雾中浮现。最前面的人蹲下身,面罩后的眼睛瞪得滚圆,视线在我空荡的右眼窝和左眼残留的灰斑间来回扫视。
“能说话吗?”他声音隔着面罩闷闷的,手套小心地避开我皮肤上未消退的菌丝痕迹,“我们是疾控中心的特别行动队。”
我想开口,喉咙却像被菌丝堵住,只能发出嘶哑的气音。手指颤巍巍地指向主控电脑屏幕,那里还闪着「菌核活性22%」的警告。
另一个队员凑近屏幕,倒抽一口冷气:“这什么鬼东西?神经共生体培养记录?队长,你看这些冷冻舱——”
手电光扫过炸裂的冷冻舱内部,江临冻结的腐尸在强光下泛着青黑。菌丝像蛛网裹住他爆开的眼眶,嘴角那丝安详的微笑显得格外诡异。
“别碰尸体!”队长厉声喝止伸手的队员,“全部样本都要隔离。医疗组,先给她注射抑制剂!”
针尖刺入脖颈的瞬间,菌核在胸腔里猛地抽搐!视野突然闪过双重影像:左眼看见穿防化服的男人推着注射器,右眼(尽管已失明)却共感到他手套下蔓延的灰斑——和宋晚瞳孔里的纹路一模一样。
我挣扎着想推开他,手臂却被菌丝残留的麻痹感禁锢。抑制剂冰冷的液体流入血管,菌核的搏动渐渐平缓,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在苏醒——无数记忆碎片像解冻的冰碴,扎进脑髓:
手术刀划开颈动脉的冰凉,不是江临的手,是戴着疾控中心徽章的手腕;
妹妹在病床上哭喊“姐姐救我”,而病房门牌写着“特殊病原体隔离室”;
年轻的我签下的不是实验志愿书,是“高活性神经携带者”检疫协议……
“剂量够了。”队长的声音突然变调,带着宋晚特有的气音韵律,“培养基需要稳定情绪。”
我猛地抬头,他的面罩反射着冷光,但脖颈侧缘的皮肤下,有什么东西正随着话音节律搏动——是菌核共感时见过的神经束蠕动态!
另一个队员掀开炸裂的冷冻舱盖,动作熟练得不像第一次接触这种装置。他弯腰检查江临尸体时,后颈防护服裂缝里露出一小块褐斑,形状和宋晚肩胛的菌核印记分毫不差。
“样本2018年系列存活率如何?”队长突然用某种晦涩的术语发问。
队员头也不抬:“七号培养基神经活性达标,已接入主网络。”他踢了踢地上僵死的菌丝,“这次污染事件能帮我们清理掉失败品。”
恐惧像液氮般灌满胸腔。他们不是救援队——是来回收实验体的!疾控中心才是菌核研究的真正源头!
我想尖叫,抑制剂却让声带瘫痪。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江临的尸体装进印着“高危生物材料”的裹尸袋,动作轻车熟路,仿佛在处理日常废弃物。
“别担心。”队长俯身,面罩几乎贴到我脸上。他眼底掠过一丝粉红孢子般的反光,“带你回‘医院’做全面净化。”
“医院”二字他咬得格外重,像咀嚼着某个阴森的暗号。记忆碎片突然拼凑出新的画面:妹妹被推进手术室时,门牌标注的正是“疾控中心神经科特殊护理单元”。
队员拽起我时,左脚踝的扭伤剧痛让我短暂挣脱。手指扒住控制台边缘,碰倒了半罐液氮。白雾弥漫间,我看到队长弯腰捡起宋晚遗落的钻戒——他擦拭戒圈血迹的动作,和江临在墓碑前如出一辙!
“Song&jiang……”他摩挲着刻痕低声轻笑,戒指在指尖转出冷光,“这代号该更新了。现在叫‘疾控中心菌核研究项目’。”
真相如冰锥刺穿颅骨:从来没有什么江临的私人复仇,所有悲剧都是疾控中心人体实验的延续!宋晚是早期实验体,我和妹妹是后续的“培养基”,而江临……或许只是被植入记忆的监管员!
他们架起我走向通风管道。经过焚化炉时,我看到炉门内侧用血画着潦草的图案:三个圆圈彼此嵌套,最中心点着红痣——和宋晚眉梢的痣位置相同。
队长注意到我的视线,面罩下传出模糊的笑声:“标志很眼熟?你妹妹设计的项目徽标。”
妹妹?!她还活着?!
冲击让我几乎瘫软。但就在被拖进管道的前一秒,我瞥见队长防护服袖口露出的手腕——那里纹着一行小字:
培养基编号∞
菌核在我胸腔突然猛跳,像被唤醒的恶魔。远处传来新的脚步声,伴随着熟悉的呼唤:
“姐姐……我来接你回家……”
声音甜腻如蜜,却让我每根神经都冻结成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