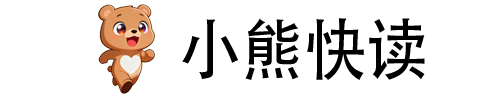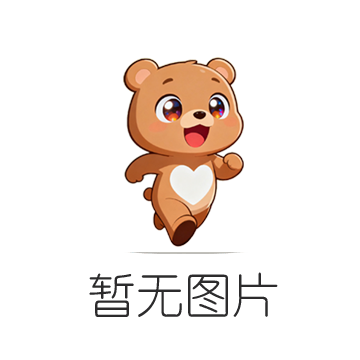冷冻舱的冷气像毒蛇的信子,舔上我的脸颊。妹妹——或者说,顶着苏念皮囊的那个东西——裂到耳根的嘴角滴下混着孢子的黏液,落在舱盖上,发出“滋啦”的轻响。她灰白色的右眼完全被菌丝占据,像一窝蠕动的蛆。
“家到了,姐姐。”她的声音像是无数个声音叠在一起,有妹妹的童音,有宋晚的柔媚,还有防化队长临死前的嘶哑。
我的手腕被她菌丝化的手指箍着,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抵抗是徒劳的,胸腔里的菌核像是找到了归宿,疯狂地撞击着胸骨,每一次搏动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,以及……一种诡异的归属感。仿佛我生来就该躺进这个冰冷的棺材。
舱盖完全滑开,更多的冷白雾气涌出,模糊了视线。但足够了,我看清了那悬浮在防腐液里的东西。
不是妹妹年幼的身体,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培养皿。
是那个布娃娃。妹妹苏念小时候寸步不离的旧娃娃,裙边都被她摸得起了毛边。可此刻,娃娃原本缝着纽扣的眼睛,左眼被换成了一颗浑浊的琥珀,里面封着一抹暗红,像凝固的血点。右眼则是一个黑洞洞的窟窿,一条沾着黑血的菌丝从里面探出来,像探寻的触须,在粘稠的液体里缓缓摆动。
“认……得吗?”妹妹的声音带着扭曲的笑意,“你送她的生日礼物。她说,有娃娃陪着,打针就不怕疼了。”
记忆的碎片像冰锥扎进脑海:妹妹蜷缩在病床上,小脸惨白,怀里紧紧抱着这个娃娃。穿白大褂的人(不是江临!是疾控中心的人!)拿着粗大的针管走近,她吓得往我身后躲,娃娃掉在地上。我捡起来塞回她手里,说:“念念不怕,姐姐在,娃娃也在陪着你。”
那时候,我以为那只是安慰。
原来,那是一场献祭的开端。这娃娃,早就成了某种……容器?
菌核在我胸腔里发出一声尖啸,不再是痛苦,而是某种共鸣。我眼前的景象开始重叠、扭曲——左眼看到的是冷冻舱里诡异的娃娃,右眼(尽管空洞)却“看”到一片深红,仿佛透过娃娃的琥珀眼睛,窥见了一个更庞大的、搏动着的意识深渊。
“母亲很喜欢这个‘家’。”妹妹伸出另一只手,指尖也变得半透明,菌丝缠绕,“她说,比冷冰冰的实验室温暖。”
她的手指触碰到娃娃的额头。
一瞬间,巨大的信息流像决堤的洪水冲垮了我的意识屏障。
不是记忆,是感知。
我“感觉”到自己悬浮在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,周围是无数闪烁的、微弱的光点,每一个光点都传来不同的情绪——恐惧、绝望、麻木、还有一丝残存的依恋……是那些“培养基”!苏软2018,李晚2021,张晚2023……所有被吞噬的神经残骸,它们的意识碎片像星辰般漂浮在这里,构成了这个所谓的“主网络”!
而在所有光点的中心,是一个巨大、沉默、贪婪的黑暗漩涡。它没有具体的形态,只有无尽的饥饿和冰冷的控制欲。这就是“母亲”?宋晚?还是……疾控中心培育出的怪物?
“姐姐,欢迎来到真正的家。”妹妹的声音直接在我脑髓里响起,充满了归家的喜悦,“别抵抗了,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你的神经活性最强,母亲会给你一个靠近中心的位置。”
冷冻舱的机械臂开始移动,冰冷的夹具扣向我的肩膀,要将我按进那浸泡着娃娃的防腐液里。那液体会溶解我吗?还是让我的神经与这个可怕的网络永久连接?
不!
妹妹缝合线崩开的嘴角,娃娃窟窿里探出的菌丝,还有防化队员融化成的粉色黏液……这些画面像最后的强心针,激起了我仅存的本能反抗。
我不是培养基!我是苏软!
我猛地低头,用尽全身力气,一口咬在妹妹箍住我手腕的菌丝上!
“呃啊——!”妹妹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,那声音里混杂着愤怒和……一丝熟悉的、属于苏念的痛呼?
咬下的地方没有血,只有喷溅出的粉红色孢子雾和断裂的、像电线般的菌丝纤维。但这一下,似乎短暂干扰了她与那个“主网络”的连接。
箍住手腕的力量一松。
几乎同时,我胸腔里的菌核发出了另一种频率的震动,不再是顺从,而是尖锐的警报!一段被深埋的、属于江临的记忆碎片,被这警报声硬生生扯了出来,塞进我的意识——
(记忆画面)
年轻的江临,躲在疾控中心档案室最深的角落,颤抖着翻阅一份绝密档案。档案标题是:【项目Ω:自主意识菌核的失控风险及紧急清除协议】。
他快速翻到某一页,上面用红笔圈出一行字:【初代共生体苏念的神经印记,是唯一能短暂干扰主网络、触发协议的关键密钥。印记载体:其执念最深之物。】
档案附着一张模糊的照片,正是那个旧布娃娃。江临的目光死死盯着娃娃的右眼窟窿。
(记忆结束)
执念最深之物……娃娃的右眼!
那个窟窿!那条菌丝!
冷冻舱的夹具已经碰到了我的脖子,冰冷刺骨。妹妹被激怒的菌丝像鞭子一样抽打过来。
没有时间思考了!
我伸出还能动的左手,不是推向妹妹,也不是挡开夹具,而是直直地、狠狠地插向冷冻舱里——插向那个漂浮的布娃娃的右眼窟窿!
指尖触到了那条湿滑、蠕动的菌丝。
“不——!”妹妹的尖啸变成了恐慌。
我用力一扯!
咕叽一声,菌丝被我从娃娃眼眶里连根拔断,断口处喷出更多的孢子和黑水。
整个地下实验室,猛地一震。
所有灯光疯狂闪烁,墙壁上搏动的菌丝网络像被通了高压电,剧烈抽搐、萎缩。头顶传来金属扭曲的呻吟,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在痛苦地痉挛。
妹妹的身体僵在原地,脸上的表情凝固在惊骇的瞬间,裂开的嘴角不再滴落黏液,灰白色的右眼也失去了光泽,像两颗腐烂的葡萄。
“念念……?”我下意识地喊出声。
她的瞳孔似乎微微动了一下,闪过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属于苏念的茫然,但下一秒,更浓稠的菌丝就从她七窍中涌出,将她彻底吞没。她像一尊融化的蜡像,软塌塌地倒在地上,化作一滩粉红色的、搏动着的粘液。
冷冻舱的夹具松开了。机械臂垂落下来,发出无力的“嘎吱”声。
我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,大口喘着气,胸腔里的菌核仍在狂跳,但那种被控制的感觉减弱了。环顾四周,墙壁上的菌丝网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、发黑,变成一碰就碎的焦炭状物质。
成功了吗?那个“主网络”被破坏了?
我看向冷冻舱里的布娃娃。它静静地悬浮着,右眼的窟窿里不再有菌丝探出,像一个普通的、被遗弃的旧玩具。那颗琥珀左眼,也失去了诡异的光泽。
寂静,死一般的寂静。只有远处管道里偶尔传来的滴水声,以及我自己粗重的呼吸。
我挣扎着爬起来,扶着冰冷的舱壁,想要远离这个鬼地方。必须离开,趁现在!
就在这时——
咕噜。
一声轻微的、像是水泡破裂的声音,从冷冻舱里传来。
我猛地回头。
布娃娃的右眼窟窿里,冒出了一个……新的东西。
不是菌丝。
是一个极其微小的、粉红色的肉芽。顶端裂开一道细缝,像一只初生的、没有睫毛的眼睛。
它轻轻转动了一下,“看”向了我。
菌核在我胸腔里,发出了前所未有的、充满渴望的悸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