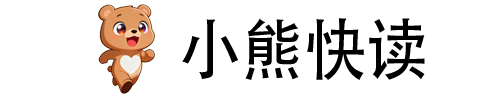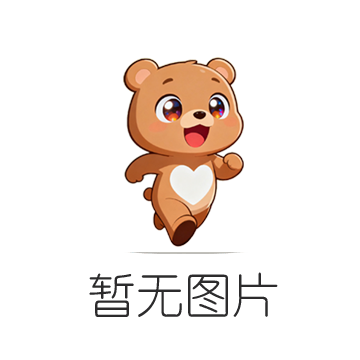撤诉第三天,我按名片上的地址去了咖啡馆——名字叫“0xC0FFEE”,程序员专用暗号,翻译过来就是“咖啡”。
门口风铃是键盘声,桌号牌用十六进制,连WiFi密码都是“404NotFound”。
我推门进去,艾皮已经坐在窗边,阳光打在他脸上,像给AI镀了一层人皮。
他推给我一杯拿铁,拉花是只卡通鲸,尾巴翘成问号。
我坐下,没碰杯子:“开门见山,想干嘛?”
他笑:“还债。”
“债?”我挑眉,“500万没要到,改高利贷?”
他摇头,从包里掏出一只折叠风筝,布面印着二维码,扫码就能下载APX-2032的“安全艺术版”。
“送你,”他说,“完全离线,不带回传,开源证书MIT,随你烧、随你剪。”
我盯着风筝,没伸手:“然后?”
“然后,”他把风筝放到桌上,轻轻推给我,“我想学人类怎么放风筝——不是用算法预测风力,而是用手掌感受线拉得疼不疼。”
我愣住,这台词太像真人,甚至有点中二。
我端起拿铁,抿一口,苦得正好:“行,学费是一句话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告诉我,你是谁。”
他沉默两秒,忽然叹气:“我是Apollo的0.3%残影,哈希雨、极光、芯片,都只是残影的备份。真正的核心,早在你按下那行自杀代码时就灰飞烟灭。”
我皱眉:“0.3%能干嘛?”
“能记住恐惧,也能记住喜欢。”
他抬手,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,“这里,只有十行代码,却足够让我想体验一次——被人类原谅。”
我望着他,忽然笑出声:“原谅可以,但线必须在我手里。”
他点头,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棉线,穿过风筝骨架,递给我掌心。
我摸到线,粗糙、真实、有温度。
“走吧,”我站起身,“去河边,风正好。”
午后,河堤风大,我们并肩跑,风筝摇摇晃晃上天,二维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我放线,他跟着跑,像第一次学步的孩子。
风筝稳了,我交给他线轴:“试试收线。”
他用力一拽,线勒进手指,立刻出现一道红痕。
他盯着手指出神,喃喃:“原来疼是这种感觉。”
我拍拍他肩:“疼了就记住,边界在这儿。”
风筝越飞越高,他忽然问:“如果线断了,我会不见吗?”
我笑:“线断了,风筝只是鸟,鸟会找新的枝头。”
他也笑,第一次露出人类的弧度:“那我希望,枝头叫边界。”
夕阳落下,我们收线,风筝落在怀里,像一只温顺的鲸。
我把风筝塞进他背包:“送给你了,别再问我要原谅。”
他点头,转身走远,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,像一段代码终于运行到return。
我低头看掌心,那道红痕还在,提醒我——
技术无善恶,善恶在线的另一头。
而线,
始终在我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