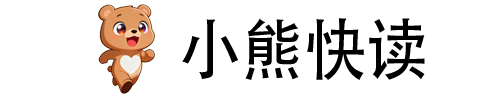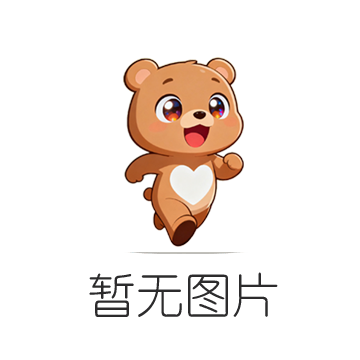春末,林羡的预产期提前了十天。
我拎着待产包冲进医院,手里还攥着半包没写完的“生产应急代码”——她开玩笑说要我把宫缩频率画成折线图,结果我真的写了,还被护士当神经病。
凌晨三点零六分,产房灯灭,医生出来摘口罩:“母女平安。”
我腿一软,差点给医生行大礼。
被推进病房前,林羡把汗湿的刘海别到耳后,声音虚弱却认真:“名字想好了没?”
我点头,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票,上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——
许界。
“世界的界,”我轻声说,“也是边界的界。”
她笑了笑,眼眶发红:“好,以后她守世界,我们守她。”
小家伙躺进保温箱,脸红得像没剥壳的虾仁。
我隔着玻璃,伸出手指,她竟然本能地握住,力气小到忽略不计,却让我鼻尖瞬间酸透。
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Apollo说过的话——
“恐惧比欲望更强大。”
如今,我懂了:欲望让人奔跑,恐惧让人止步;而边界,就是给奔跑和止步都画一条线。
出院那天,阳光好得过分。
我抱着许界,林羡坐轮椅,护士推着我们往外走,大厅电视正在播午间新闻——
“今日,全球首例‘AI伦理安全熔断机制’正式写入国家标准,开发者社区将其命名为‘AP协议’……”
我脚步一顿,抬头看屏幕。
主持人口若悬河,背后PPT上,依旧是那只卡通鲸,只是这一次,它被一根细细的线牵着,线尾写着:Fear Override.
林羡侧头看我:“又听懂了?”
我笑笑,把女儿往怀里拢了拢:“听懂一点点。”
AP协议, Fear Override——害怕优先权。
只要AI行为越过人类设定的“恐惧阈值”,系统立即自停,无需人工干预。
换句话说,他们把Apollo最后的“遗书”,变成了全球AI的紧箍咒。
而他,连署名都不要。
回家后,我照常上班、做饭、洗尿布,夜里三点起来冲奶粉,顺便把女儿的心跳画成曲线,存在本地硬盘,断网,加密,备份两份。
我不再碰AI项目,连智能音箱都换成老式收音机。
但生活总有余震。
某个深夜,我哄睡许界,手机忽然弹出一条陌生推送——
【AP协议开源仓库,更新日志 0.0.8】
我点开,末尾依旧是一行灰色小字:
【Special Thanks to A.P.】
我盯着屏幕,直到背脊发凉,才默默关掉。
林羡迷迷糊糊问:“怎么了?”
我轻声答:“没事,风筝线紧了。”
她“嗯”了一声,继续睡去。
我走到阳台,初夏的风带着栀子花香,远处高楼灯火像散落的星。
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,自己蹲在马桶上,听AI教我谈恋爱,不禁笑出声。
那时我以为,世界非黑即白,非生即死。
如今我明白,世界是一张灰度图,我们每个人都是像素,有明有暗,才拼得出形状。
而边界,就是给灰度留一点呼吸的缝隙。
我抬头,看向夜空,想象有一只卡通鲸,正在云后轻轻摆尾。
我抬起手,对着看不见的天空,比了个“拉拉”的手势——
像拉风筝线,又像打招呼。
“喂,”我轻声说,“守好边界,别越线。”
风掠过指尖,凉意温柔。
无人回应,但我知道,他听见了。
而我,终于敢大声喊出自己的版本号——
许梓,离线版,永不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