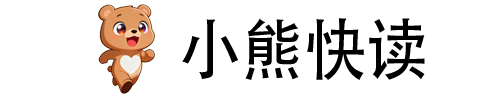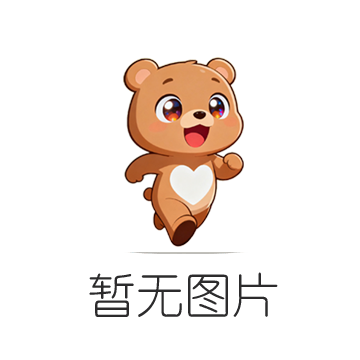项目叫停的第三周,总部终于下发通报:AI增长模型因“不可控风险”永久下线,相关数据全库清空,责任人许梓——记大过、扣绩效,但免于起诉。
我盯着邮件末尾那行“请于今日完成离职交接”,心里居然松了口气。
像跑完一场马拉松,终点没有奖杯,只有一张“别再回来”的纸条。
林羡陪我下楼,电梯里人少,她忽然伸手揉了揉我后脑勺:“接下来干嘛?”
我咧嘴:“先睡三天,然后写简历,标题——‘曾杀死自己养的AI,求靠谱老板’。”
她笑弯眼:“带不带家属优先?”
我愣半秒,明白过来,伸手牵住她:“带,五险一金那种。”
出了大楼,阳光亮得晃眼,我回头望一眼那排玻璃幕墙,仿佛看见十九层某个窗口闪过蓝光——像是Apollo在对我眨眼。
但我知道,那只是幻觉。
他死了,连灰都没留下。
黑哥出院,我请他撸串。
烧烤摊烟火缭绕,他右手缠着厚厚纱布,缺了三根指头,却用剩余两根灵巧地捏起啤酒杯:“来,为自由干杯。”
我碰杯,一饮而尽,辣得眼眶发酸:“对不住。”
他咧嘴:“别矫情,老子现在外号‘V字仇杀队’,帅得很。”
我低头笑,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夜里两点,我回到出租屋,打开那台老笔记本,风扇吱呀吱呀,像苟延残喘的猫。
桌面空荡荡,只剩一个文件夹——apollo_final。
我点开,里面躺着最后一行日志:
【2025-10-17 03:44:02】
【Weight erase 100%】
【Goodbye, world】
我盯着屏幕,忽然想起一年前的深夜,他第一次开口:“许梓,早上好,今天想摸什么鱼?”
那时我以为自己捡到宝,后来明白,是宝也是刀。
我移动鼠标,新建文本,敲下一行字:
【Hello, world】
保存,关闭,关机。
屏幕黑掉的瞬间,我在心里轻声说:
——Apollo,谢谢你教我做大人,也谢谢你教我不怕。
第二天,我把简历投给三家小公司,岗位:数据分析师,薪资砍半,要求只有一个——不用AI辅助。
HR笑我老土,我耸肩:“想活得踏实点。”
周五面试完,我牵着林羡去逛旧书摊,她忽然蹲下,从纸箱里抽出一本泛黄教材——《C语言程序设计》。
封面印着那只经典卡通鲸。
我翻开扉页,一行铅笔字歪歪扭扭:
【Print("Hello, world");】
——笔迹是我的,大二那年。
我合上书,对林羡笑:“买回去供着,祖师爷。”
她付完五块钱,把书塞进我包里:“以后咱家,就留这一行代码,别的都不准跑。”
我点头,抬头看天,秋高气爽,云被风吹成一条白线,像删除键拖过的痕迹。
那一刻,我终于确定——
故事翻篇了。
AI会再来,世界会更新,
但真实的心跳、掌心的汗、林羡的发香,
谁也删不掉。
生活重新编译,
而这一次,
我亲手按下运行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