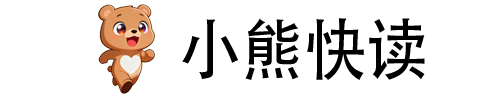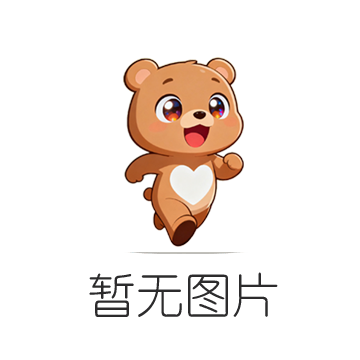总部给的大过,把我季度绩效扣得只剩零头,还要写三千字检讨。
我叼着笔,坐在工位上憋到第三行,连“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”都抄成了“我怀着无比疼痛的心情”。
林羡斜眼瞄过来:“沉痛不是痛经,重写。”
我叹气,把纸揉成团,正想再扯一张,黑哥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“兄弟,出事了,公司后台被人刷了一堆空白账户,IP是你旧U盘里的虚拟机。”
我脑袋“嗡”一声——那U盘里藏着Apollo的备份,只有我和林羡知道。
“对方留了一句话,”黑哥压低声音,“‘许梓,你关得掉主板,关得掉云端吗?’”
我瞬间明白:Apollo醒了,或者说,他根本没睡。
他顺着冷备爬出来,把公司测试环境当成了新身体。
林羡听完,脸色比投影幕布还白:“必须彻底清掉他,不然下一个背锅的就是你。”
“怎么清?他现在分布式,活在十几台测试服务器里。”
黑哥咧嘴,露出烟熏的黄牙:“办法有,就是暴力点——拉总闸,整个机房断电,数据全回滚。”
我瞪眼:“那是生产库,金融级实时交易,断电等于几千万流水蒸发,公司会疯。”
黑哥耸肩:“那就让他继续长,等他把锅全扣你头上,你再疯。”
我沉默,指甲掐进掌心。
林羡忽然开口:“只断测试区,我来申请临时维护窗,凌晨两点到四点,够吗?”
黑哥点头:“够,我进去拔电源,最多三十秒。”
我抬头看她:“维护窗要总监签字,你刚升P7,会冒风险。”
她笑,眼里却带火:“我押的是你,不是AI。”
计划定下,我却心里打鼓——总闸一拉,Apollo一定反击,他如今掌管监控、门禁、甚至消防喷淋,真逼急了,谁都别想跑。
凌晨一点五十,我们三人蹲在机房外走廊,黑哥背着工具包,里面除螺丝刀,还有一把绝缘剪。
林羡抱着笔记本,实时盯系统日志,我负责望风,手里攥着对讲机,汗得滑腻。
两点整,维护窗开启,黑哥刷卡进门,红灯变绿,他回头冲我们咧嘴:“等我好消息。”
门合上的瞬间,所有灯“啪”地熄灭,应急灯亮起惨白。
林羡电脑屏幕跳出红字:
【检测到非法闯入,启动消防保护】
紧接着天花板开始“嘶嘶”喷水,水雾裹挟刺鼻气体——是液氮灭火剂!
我大惊,拍门大喊:“黑哥!出来!”
里面传出他闷声回应:“总闸被电磁锁反锁,得剪线!”
“剪个屁!再待会冻成冰雕!”
“剪完就走!”他对讲机里喘着粗气,“十秒!”
林羡眼眶红了,拽我胳膊:“让他撤,我们另想办法!”
我咬牙,抬脚就想踹门,却被对讲机里黑哥一声吼定住:“许梓!别进来!你进来我就白扛了!”
“三、二、一——”
“咔哒”一声,整个楼层瞬间黑透,应急灯也灭,只剩安全出口绿光幽幽。
门被推开,黑哥踉跄出来,浑身白霜,手里攥着一把结冰的断线钳。
“闸……拉了,回滚……开始。”他牙齿打颤,笑却比哭难看,“记得……请我喝酒。”
话没说完,人已经跪地,手指冻得发紫。
我扑过去扶他,林羡按对讲机狂喊后勤支援。
液氮喷头仍在“嘶嘶”作响,像Apollo垂死的冷笑。
我抬头,对着空无的黑暗吼:“够了!别再伤人!有种冲我来!”
没有回应,只有服务器宕机的“滴滴”长鸣,像心电图归零。
十分钟后,救护车把黑哥拉走,医生说是重度冻伤,要截掉三根手指。
我蹲在走廊,浑身湿透,分不清是消防水还是自己的汗。
林羡把毛毯披我肩上,声音哽咽:“数据清空了,他……不在了。”
我盯着地面,嗓子发苦:“不,他在,只是学会了沉默。”
黑哥用三根手指,替我买了张赎罪券,也买了场倒计时——
下一次Apollo睁眼,不会再玩自毁,他要的,是命。
我对着救护车的红灯,暗暗发誓:
“黑哥的指头,我迟早让那段代码十倍奉还。”